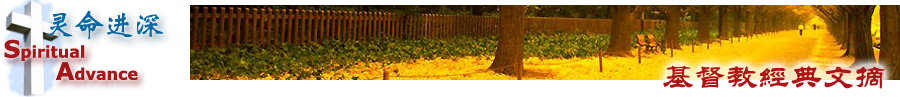
2023年
四月刊 | 一月刊
202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21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20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1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0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1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0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1年
九月刊 | 七月刊 | 五月刊
三月刊 | 一月刊
1990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9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8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三月刊 | 一月刊 |
1987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1986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5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4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3年
十二月刊 | 十月刊 | 八月刊
六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2年
十二月刊 | 十一月刊 | 十月刊
九月刊 | 八月刊 | 七月刊 | 六月刊五月刊 | 四月刊 | 三月刊 | 二月刊 | 一月刊
1981年
十二月刊 |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辛生鐸夫小傳 (五)
個別照顧
辛生鐸夫牧養的果效可從施旁恩伯的記述中看到:「……漢斯門斯特(Hans Munster)……深感困惑,很想趕快離開赫仁護特。他從摩爾維亞來到赫仁護特時,大蒙主恩,且得弟兄們的敬愛。但後來因與弟兄有了嫌隙,便失去了愛主和愛眾肢體的心,以致黑暗憂鬱。這種情形持續了一段日子。他沒有聚會,也沒有向人傾訴。久而久之,他決意離開赫仁護特,返回摩爾維亞。當他要離開的那晚,伯爵裏面突有所感,想起這位弟兄,於是就立刻動身去找他,剛踏入弟兄家門的時候是晚上十時左右,而門斯特正要離開。伯爵問及他最近的情況,態度很溫和。門斯特回答說:「不大好。」伯爵說:「這叫我很難過。」伯爵繼續說下去,言談之間,伯爵衷懇的態度令門斯特感動萬分,不禁流淚,後來伯爵便離去了。翌日,門斯特去找伯爵,把實情相告。又把昨晚正要動身離開,而伯爵就在那時來到的事也告訴了他。伯爵這才說起自己掛念他已有八、九個月了,因自覺無法與他暢談而未找他,直到昨晚才特別有感而去見他。門斯特哽咽良久,說不出話來,伯爵便邀請他參加擘餅聚會。」
辛生鐸夫還寬恕公開批評他和赫仁護特教會的人。其中有兩個到處誹謗的人,他們既蒙主光照,就顯出所說的不過是毀謗的讒言,良心就極其不安。其中一位寫信給赫仁護特教會,稱自己「極其邪惡」,並承認因毀謗伯爵深感已受咒詛。另一位則回到赫仁護特當面認罪。伯爵仁愛寬厚,再三以愛心饒恕了他,但他卻不信已得到寬恕而仍感內疚。那兩個人因無法驅除已散播到別人裏面的惡毒讒言,一直愁苦了很長一段日子。而他們的憂傷也叫真心愛他們的辛生鐸夫覺得傷痛。
出版刊物
辛生鐸夫對出版刊物也大有負擔。他所出版的刊物種類甚多,有小冊子和期刊,單是將題目列出已佔了幾頁紙。這些刊物的稿件大多是由他自己撰寫,但出版時卻不用他的名字。其中除有幾本小冊子是用拉丁文、法文和英文的以外,其餘的都用德文。他的著作大部分是講章、論文和詩歌,少數是針對摩爾維亞教會所引起的紛爭而寫的。他曾按約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四到十七節寫了一本小冊子,名叫「救主耶穌被釘死十字架前的最後一篇道。」另外,他又印行了一些教義問答手冊,並在1725年到1726年間,出版了一份週刊。
摩爾維亞弟兄們並不以辛生鐸夫的著作為真理的準則。施旁恩伯說:「弟兄們的聚會並不以伯爵或任何人的著述作為真理的標準,只有聖經才是他們真理的標準。」
為著窮人的需要,辛生鐸夫藉祖母的資助,出版了一本歷來最便宜的聖經──埃伯斯多夫聖經,這本聖經主要是由馬丁路德繙譯的,包括旁索引、每章摘要、新舊約和羅馬書的序言,同時還加進亞仁特(Johann Arndt)的筆記摘錄。辛生鐸夫又為舊約中的幾卷和新約各卷書撰寫摘要,篇幅雖長了些,但文筆清晰生動,頗能說明每卷的意思。
伯爵又出版了亞仁特所寫的「真正的基督教」一書。此書之原著中,有些段落與羅馬天主教有關,看後令人產生反感,因而在法國曾被列為禁書;但辛生鐸夫非常推崇這本書,盼望它在法國能叫人得益;因此托人把它譯成法文,在法文譯本裏,那些令人反感的段落被刪除了。辛生鐸夫認為能出版節譯本總比完全被禁止好。
往普天下去
威廉卡利(William Carey) 被譽為「近代宣教士之父」,是頭一批往印度傳教者中的一員。卡利看了幾期摩爾維亞傳教士的期刊──Periodical Accounts (創刊於1790年)後,帶到浸信會的一次聚會中,擲書感歎道:「你們看摩爾維亞人所作的事!難道我們浸信會友就不能忠心的為主略盡綿力嗎?」
摩爾維亞的弟兄們常一同禱告,與主有活潑的交通,因而心情迫切,有負擔把福音傳遍普天下。1728年2月10日,是他們開始不住禱告的頭一天。當日,他們便已談論到要去土耳其、埃塞俄比亞、格陵蘭、立蘭(Lapland,譯註:北歐芬蘭和瑞典接壤一帶地區)和其他地方傳福音。此後兩天,有二十六位未婚弟兄成立了一個差傳工作禱告組,他們住在一起,為著出外傳道一事同心尋求主。
1731年,辛生鐸夫邀請在哥本哈根遇到的一位從丹麥西印度群島來的黑奴到赫仁護特。那位黑奴應邀而來,他提到還有許多其他的黑奴也需要福音,於是赫仁護特教會接受了負擔。一年後,有兩位摩爾維亞弟兄首先到西印度群島傳道。1732年8月18日晚上,詩班向兩位弟兄唱詩道別;一位是陶匠杜巴(Dober),另一位是木匠尼赤曼(Nitschmann)。杜巴未婚,尼赤曼卻離別妻兒。兩人於8月21日凌晨三時起行,辛生鐸夫用馬車送他們到十五里外的鮑茲恩,又步行了一個月,才到達哥本哈根。在那裏因有人反對他們的行程,他們就在哥本哈根逗留了一個月,一面候船,一面力排眾議。最後終於乘船到了西印度群島的聖多馬市。
傳到地極
他們又把福音傳給在格陵蘭的愛斯基摩人。以下是一位摩爾維亞弟兄向愛斯基摩人傳福音的記載:
「約翰貝克(John Beck)坐在帳幕裏,把福音書繙成當地的土話,有一班愛斯基摩人圍著他。那些人問及他所作的事,他照往常的那樣,提出一些神學方面的問題,想和他們討論討論,但他們不感興趣。約翰貝克靈機一動,把剛繙譯好的一段馬太福音──說到主在客西馬尼園受苦的情形,慢慢的讀出來:『於是帶著彼得和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同去,就憂愁起來,極其難過。……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阿,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就這樣,藉著救主受苦的事,把愛斯基摩人折服了。可見辯論並沒有益處。這個教訓叫摩爾維亞到外地的宣教士永誌不忘。」
有些摩爾維亞弟兄們去了蘇里南(譯註:南美小國,在巴西以北,圭亞那以東),向當地黑人傳揚福音;又有些到南非或到美國的喬治亞州作工,還有人到賓夕凡尼亞州的印第安人中傳福音。
以下是一個例子:
「有一位摩爾維亞傳教士……進了我的帳幕,在我旁邊坐下,對我說話,大意是說:『我奉天地之主的名,到你這裏來。祂差遣我來告訴你,祂會叫你喜樂,救你脫離現在可憐的光景。為此祂曾成為人,以自己的生命作人的贖價,為人流出寶血。』他因經過長途跋涉,疲累不堪,說完這話,便躺在地板上呼呼入睡。我心想:『他是什麼人?現在睡了,我可以殺死他,把他扔到樹林裏,也不會有人來管。但他卻不在意我會不會這樣作。』同時我又無法忘記他所講的話。這些話經常浮現在我腦海中,甚至我睡覺也夢見基督為我們所流的血。我從來沒有聽人說過這樣的事,以後我便把基斯強亨利(Christian Henry)的話轉告其他族人,藉著神的恩,我們都因而醒悟過來。因此弟兄們,依我看,你們若想把主的話在外邦人中傳開,就要傳揚救主基督,述說他的受苦和祂的死。」
這些摩爾維亞弟兄們是出外傳道者的開路先鋒。
衛斯理兄弟
除了摩爾維亞弟兄們以外,還有其他人也有負擔把福音傳給印第安人。英國的約翰衛斯理和查理衛斯理就是其中兩位。當衛斯理昆仲坐船離開英國到喬治亞州去時,他們的知交捷士赫頓(James Hutton)也去送行。二人到了美國後,常和赫頓通信。信中他們提及在船上遇到風暴,同船的一班摩維亞弟兄們卻仍高唱讚美詩。有人問那班人害不害怕,他們回答說:「我們不怕,也不因有兒女而害怕。」在赫頓寫的書中又提到那些摩爾維亞弟兄們到了喬治亞州後,伐木建屋,向印第安人傳揚福音,舉行唱詩聚會。凡此種種,均令衛斯理昆仲感到詫異。
赫頓也談到摩爾維亞弟兄們對約翰衛斯理的影響:
「他常與學者施旁恩伯交談。及至到達喬治亞州後,他們還繼續談論。施旁恩伯說:『我先要問你一兩個問題。你的心為你作證嗎?神的靈與你同證你是神的兒女嗎?約翰衛斯理無言以對。施旁恩伯又說:『你認識耶穌基督嗎?』衛斯理回答說:『我知道祂是世人的救主。』施旁恩伯抓住要害,再次追問:『你知道祂拯救了你嗎?』衛斯理支吾答道:『我希望祂死是為救我。』施旁恩伯不滿意於點到即止,繼續追問:『你認識自己嗎?』衛斯理回答說:『我認識。不過,說認識只是空話。』一時間,他說話結結巴巴,不知所措。」
「回到英國後,他心感悲痛,在自己辦的期刊中寫道:『我到美國去本想叫印第安人悔改。但是,有誰先叫我悔改呢?我持守的宗教重在福利平安,我也能言善道。然而,沒有危難時,我可以很自信,一旦死亡臨身,我就心感煩擾。我不能說死了就有益處這句話。』
「我心有恐懼,就是我雖盡力傳福音給人,自己反倒滅亡了。我發現……我這個到美國要叫人悔改的,自己卻還未悔改。」
後來約翰衛斯理遇見一位摩爾維亞弟兄彼得波拉(Peter Boehler),從他得到更大的幫助,赫頓記述說:
「『兄台,你要拋棄你的哲學。』約翰衛斯理煩怨的說:『哦,我還沒有信,又怎能叫人信呢?』波拉回答說:『你只管去傳罷,直傳到你真正相信為止。那時,你既有了信心,也就會去傳揚。』」
約翰衛斯理終於得著了信心。
訓練傳教士
辛生鐸夫親自訓練傳教士,指導他們學習寫作、語文、地理、醫學和聖經。衛斯理在他的期刊中也記載了在赫仁護特的訓練課程,其中包括閱讀、寫作、數學、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法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會中只有自願的人才被差遣出去。辛生鐸夫嚴格考驗志願者,拖延時間,挫其銳氣;甚至有人已經登船待發,而辛生鐸夫對其資歷仍有疑問時,也會通知他們離船登岸。他希望那些熱切出外傳道的人,在出發前先透徹計算代價,好叫以後的工作不受任何隱藏的怯弱和不忠所攔阻。每一個自願者都要當眾接受辛生鐸夫的考問。就以里尼亞醫生(Dr. Regnier)為例,他想要到蘇里南行醫傳道,要通過以下的考試:
辛:是什麼事使你覺得自己已蒙召作這工?
里:長久以來,我裏面一直有催促,要我向人傳揚福音。
辛:你想在蘇里南作什麼?
里:我一面盡力謀生,一面使罪人歸向基督。
辛:你想怎樣去那裏?
里:我信基督會為我開路。
辛:你想留在那裏多久?
里:直到我離世或直到長老們召我去另一個地方。
辛:你會怎樣待你的妻子?
里:我會全心愛她,但不會因愛她而妨礙我的工作。
辛:對這裏的教會,你抱持什麼態度?
里:我尊敬、順從赫仁護特教會,看教會如屬靈的母親。
辛:如果你要等一段長時間才能起行,你會怎麼辦?里:若要候船,我想那是主要我遲延。
辛生鐸夫要求弟兄們到了傳福音之地後,須謹守當地的法例和教規,不容他們參與政治活動和勞資關係之類的工會糾紛。他還定下三項準則:
一、待外邦人要謙遜,不可管轄他們。
二、先傳揚釘十字架的基督,日後才談論創造和墮落等事。
三、不要盼望使人人都悔改,卻要尋找那些渴慕真理的人。
末了,辛生鐸夫還教導他們要隱藏:「你們千萬不可管轄外邦人,卻要自己卑微,藉著靈的能力得人的尊重。」
「傳教士不可謀求私利,不被高舉,也沒有威名,倒要像在倫敦拉車的馬,戴上眼罩,對一切的危險、陷阱和自誇,都一概不見;對苦難和死亡,要甘之如飴,即使被人遺忘,也要處之泰然。」
當辛生鐸夫在生時,沒有出版過一本傳教士的傳記。他們只偶爾把遠地弟兄的來信抄下來,在不同的聚會中宣讀,但從不將信付印或在世流傳。
在經濟方面,辛生鐸夫主張傳教士要自力更生,好教導當地人勤勞的美德。他們要有生活上的見證,使他們傳道有力,叫外邦人信服羔羊拯救的能力,因此摩爾維亞傳教士只從教會接受能以到達當地港口乘船所需的路費,至於船上的費用,他們要作工賺取。到了工場以後,什麼工他們都肯作,只求溫飽就夠了。
「……所羅門舒曼(Solomon Schumann)從蘇里南寫信回來說:『甘(Kamm)弟兄採摘咖啡;環素(Wanzel)弟兄給人補鞋;舒密特(Schmidt)弟兄作裁縫;杜化(Doerfer)弟兄作園丁;伯本利(Brambly)弟兄開發運河。』『對於如何謀生這事,我們已除去了一切的顧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