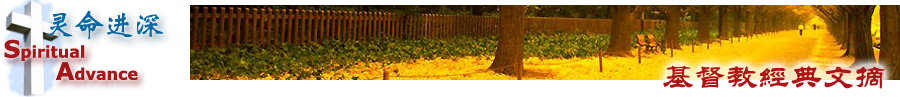
2023年
四月刊 | 一月刊
202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21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20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1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0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1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0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1年
九月刊 | 七月刊 | 五月刊
三月刊 | 一月刊
1990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9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8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三月刊 | 一月刊 |
1987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1986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5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4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3年
十二月刊 | 十月刊 | 八月刊
六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2年
十二月刊 | 十一月刊 | 十月刊
九月刊 | 八月刊 | 七月刊 | 六月刊五月刊 | 四月刊 | 三月刊 | 二月刊 | 一月刊
1981年
十二月刊 |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辛生鐸夫小傳(二)
遊歷歐洲
當時貴族子弟受教育,必須遊歷歐洲大陸。辛生鐸夫在1719-1720年間週遊歐洲。當他經過杜塞多夫城的時候,他向主祈求更多交通於祂得苦難。他在荷蘭接觸到更正教的神學家和其他不屬更正教的基督徒,因而清楚看到所有基督徒在基督裏是聯合為一的。
在法國,他遇見樞機主教諾愛立(Noailes)辛氏後來用拉丁文寫了一篇論文給他,論到基督作我們的義的功勞,他寫道:
「神若來審判罪人,人惟有藉著信,在主的寶血之上,得著耶穌為義,才能站住。我們得救不是由於教皇或任何人,卻完全在於基督的功勞。」
因他們都愛主,所以他感到與這位紅衣主教的關係很密切。
遊覽巴黎時,他對一般旅遊勝地不感興趣:
「附近的凡爾賽有不少宏偉的建築物和花園,但他到那裏只看了幾小時就覺得夠了。反而在Dieu酒店內有千百個病人得到照顧,叫他深受感動。」
辛氏在巴黎住了不久,但卻很不尋常。他說:
「我週遊四方,但我多踏足世界,基督卻更堅定的保守我。我尋找這世界的大人物,對他們述說救主的恩慈和美善。我遇見他們往往是在意料之外的。對那些不可信託的人,我很有禮貌;對那些熱衷於引誘我的,我保守自己,並且一有機會就糾正他們,像我在大學時一樣。當日所結的果子,我現在仍然得享。我與主商量每一件重要的事,世界對我沒有影響,因為雖然外表上我和別人沒有分別,但我在巴黎不跳舞、不玩紙牌。許多認識我的人,認為我已誠心奉獻,其他不太明白我的,就說我是敬虔派;但真正稱為敬虔派的人,卻認為我並不合格。」
施旁恩伯說:
「他的言行表明他反對一種想法,就是居高位的信徒能比別的基督徒更自由。他堅守習慣,繼續在主日實行禁食;從三時至七時半,遠避群眾,與主交通,雖確有不少攪擾引他改變習慣,但他為要與主交通,仍堅持不懈。」
辛氏有驕傲的難處。施旁恩伯說:
「……有時他深受驕傲所困,……他說到多次在事後深深自責,……好叫他更謙卑。他提到有一天在宮廷裏沒有受到該有的優待,因而向管家投訴,……他要求得著滿意的看待,就立即得著了。但過了不久,他反覆思想這件事,發現自己的驕傲仍未除掉。他為此跪在主腳前流淚祈求,要得主的寬恕和恩典,並欣然放下了他的特權。辛氏說:『我答應主只清心跟隨祂,完全棄絕世界,不要尊貴,不受高舉。從那時起,我那個決定一直沒有改變,而基督的責備也常帶給我喜樂。』」
1719年尾,他患重病,幾乎要死,但他一心尋求主,只切慕快被主接去,絕沒有想要求主延長的他的壽命。不過,主保留了他的性命,在教會的恢復中使用了他。辛氏寫道:
「我沒有想到會看到第二年的來臨,……創造我的主又給了我無盡的恩賜,我都衷誠感領了。祂救我脫離敗壞的轄制,不然我會成為敗壞的奴僕。我恨惡從前的懶散,以致過了許多虛妄的日子。我懇求主耶穌叫我有分於祂的形像和樣式。」
後來在離開巴黎的時候,他感到信徒的派別雖然不同,但大家都有共同的信仰。
受 聘
週遊歐洲回來後,他受聘在德斯頓(Dresden)市作律師。每逢主日下午三時到七時,他把在德斯頓的家開放,用來聚會。施旁恩伯曾提到當時的情形:
「他堅持藉著神的恩,並倚靠基督,作為他盼望的根基,並且在言行上,勇敢地表明祂,以致世人再不希冀引誘他改變立場。他誠心繼續他最大的職志,就是傳揚福音,並因與貧苦、樸實的神的眾兒女來往,而感到滿足。」
「他住在德斯頓的時候,他的家在主日一直有聚會,……內容沒有別的,就是教導和親切的談論新約中的話語,然後一同禱告、唱詩。公爵回想那段日子說:『我們在主裏喜樂,老幼都像小孩子般坐在一起。凡在我們中間顯露學識的,我們都忍耐包容,等候以活的例證加以開導。』」
在德斯頭,他以佚名出版一份刊物,名叫德斯頓蘇格拉底(Dresden Socrate)。 第一次在1725年出版,目的在接觸有組織的教會以外的基督徒。這份週刊第三次出版時就給政府充公了,直到公爵承認自己是刊物的作者時,才獲准繼續出版。辛氏在這份刊物上暢所欲言,施旁恩伯說他:「……立論驚人,辭鋒厲害」。他想引導信徒真正經歷基督,而脫離虛有其表。他責令信徒要作真基督徒,否則就不要再稱為基督徒。
購買大莊園和結婚
1722年4月,他繼承了祖業,就買下一個大莊園,包括伯佛爾斯杜夫(Berthelsdorf)的舊村莊, 目的在「培植主的美好園子」。他希望那園子成為一個避難所,收容各處不同身分、不同宗派受迫害的基督徒。
在買下莊園的同年,辛氏與雷斯女伯爵(Erdmuth Dorothea Von Reuss)結婚,為此他寫了一首詩歌,描寫基督對教會的愛。談到他的婚姻,辛氏說:
「我絕不會以世俗的方式結婚;也不會選擇與世同流的人作配偶。」
1722年9月7日,在他與女伯爵結婚前不久,他寫信給祖母說:
「將來難免有困難,因為她嫁給我這個窮人,我想她只好過一個捨己的生活。她要像我一樣拋棄對地位和富裕的想望,因為那些並非屬天的東西,只是人類虛榮的產品。她若想幫我,就必須投身於我人生的惟一目標,就是為基督賺得靈魂,並為此被人輕視和辱罵。」
他又寫信給未來的岳母:
「我預料婚後會有許多困難,因為不管誰嫁了我,都只有貧窮。我親愛的雷斯女伯爵不僅要與我同過捨己的生活,還得與我配搭,為著我人生最大的目標去幫助人,為基督得著靈魂,並蒙羞受辱。……」
伯爵夫人是一個好幫手,也給辛氏適當的平衡:
「她在家中沒有舒適或私人的生活。她常從早上六時到晚上十一時,忙著服事到她家來的弟兄姊妹。她私人的角落只有一張桌子和簾子,她很少到那裏歇息,而且每次去都說抱歉。她不斷工作、辦事、寫詩、聚會,在姊妹中間盡屬靈的職事,……她和丈夫一樣,從不花錢在小事或虛有其表的裝飾上;但『為了幫助貧困者,或當神的旨意有需要時,她就大量捐輸,往往超過她能力所及』;這一面她又和丈夫一樣。」
約翰霍姆茲(John Holmes) 說,伯爵和夫人「同心同意,……決意奉獻自己、兒女、時間和財寶給基督,並要服事祂。」
歡迎移民來到
摩爾維亞和波希米亞的反改教運動,帶來了可怕的影響──德皇查理六世下令鎮壓;聯合弟兄(United Brother)們被迫逃難,離開故鄉。他們起初逃到波蘭,後又分散到奧地利。
辛生鐸夫當時住在德斯登,知道流亡者已從摩爾維亞來到。在流亡者中,有一位名叫基斯強.大衛(Christian David)的, 此人卓越不凡;施旁恩伯對他有如下記述:
「他年僅八歲,便已尋求魂的安息。他向人訴說他的苦惱,又盡力照別人的勸勉而行,但都沒有用。長大後,他到處遊歷,曾在格爾利次當熟練技工,就在那裏,他聽見了久所渴慕的話,從此開始努力研讀聖經,……他與辛生鐸夫伯爵漸漸相熟,……他告訴伯爵有關摩爾維亞弟兄們所受的壓迫,並看到辛生鐸夫熱心事奉主,願意收容那些因憑良心行事而受壓迫的人。大衛反回摩爾維亞,向弟兄們說,辛生鐸夫會收容他們,因為他瞭解他們離開故鄉的本意,乃是要尋找一個可憑良心生活,按真理而行的地方;他們因著神的恩典,已認識了真理。」
有一班摩爾維亞的信徒聽從大衛的話,就來到辛生鐸夫的莊園。在1722年6月17日,這些流亡者開始伐木建屋。伯爵知道他們已經來到,因他接到他們的陳情書,其中寫道:「吾等深恐因在此建造新居而牽累伯爵,謹此懇請施恩庇護,協助吾等貧困小民,以仁愛予以接待。吾人必因汝之善行,懇求全能之神,賜福予汝之魂與身子……。」
辛生鐸夫同情他們,願意暫借莊園給他們使用,直到他們找到定居的地方為止,但這些流亡的人卻有不同的想法,他們準備在辛生鐸夫的莊園長久住下去。大衛等人行動迅速,竟在一個月以後就擬定了定居的計劃,連辛生鐸夫也毫不知情。但辛生鐸夫還是贊同了他們的意願:
「在1722年12月底,辛生鐸夫首次與妻子同遊,……正要離開伯佛爾斯杜夫附近一個名為斯特瓦德爾的村莊,看見在樹林裏的路旁有一所房子,有人告訴他,是由摩爾維亞來的人在他的莊園上蓋的。他大感喜樂,進了那房子,熱切的歡迎他們,與他們一同跪下感謝神,並誠心為那地方祝福,求神伸手保祐,又勉勵住在那裏的人,使他們對神的恩惠和信實滿有把握,……現在伯爵最關心的是,他所收容的人都能認識主。」
這些移民把他們建造第一所房子的地方起名叫「赫仁護特(Herrnhut)。他們這樣命名,乃是希望蒙主看護,也為主守望。
辭職和遭反對
辛生鐸夫在德斯登受聘為法院議員雖然他的同僚盡力使法院生活合其心意,但他曉得「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雅四4)施旁恩伯描述他的情況說:
「對於朋友的好意,他感到為難。朋友們歡喜把他抬到更高的地位,但他書面懇求朋友們不要這樣作,特別是在聽到要被推舉為宮廷大臣時,就更加以懇辭。他自稱完全不適合種要由屬世的人來作的事,那些事必須有屬世的智慧;而他既不屬世,也沒有那種智慧。他熱切渴慕的,乃是成為神的兒子和真實的基督徒。他這種性格,使他厭惡法院所給人的福樂和世界的榮耀。」
辛生鐸夫深知當他外祖母在世之日,他仍要勉強就任此職,因為她盼望辛生鐸夫留在政府裏辦事。辛生鐸夫二十七歲時,外祖母去世了。他跟母親和繼父商議後,就正式辭去官職。在一封1728年寫的信中,他述說去職的感受:
「我感到難以繼續擔任此職,因我惟恐在每天處理事情時,我的行事為人與神的話相違背。主說:『他們有大臣操權,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這證明那工作對心靈的工作有礙,而宗教是我惟一的目標。有時我似乎被公民的義務所征服,……但我本該被苦難和降服所勝;因我的眾弟兄已經歷了羞辱和苦難,而將來可能會有更多同樣的苦難臨到我。」
有人在德斯換出版小冊子,間接攻擊辛生鐸夫。其實在此之前已有人反對他所主編的德斯登蘇格拉底週刊,現在更有人懷疑他是否已經得救。一般人認為,凡是悔改信主的人,必定有對所犯的罪產生焦慮和傷痛的經歷,但辛生鐸夫曾公開承認他起初經歷救恩時並沒有為罪哀痛的情形,別人就判定他沒有真正悔改信主。辛生鐸夫花了很長的時間來研究這事。他切望有那種罪的經歷;但每逢他為這事仰望主時,他所經歷的只是覺得自己是個可憐的罪人,跪在主的面前,緊靠著祂。他因而斷定,神救贖人的本意,乃是要得救的人愛那不能看見的主,並且相信祂,如同看見祂一樣。